《北方文学》2024年第5期刊发张建鲁主席小说《失踪的战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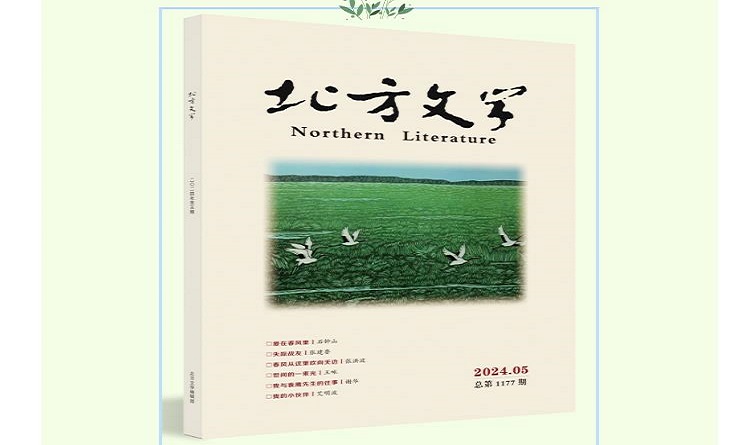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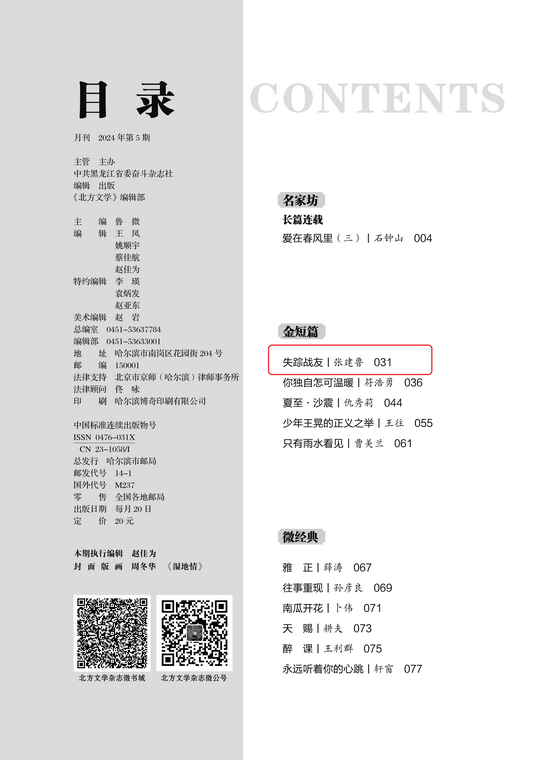
失踪的战友
(原文刊于《北方文学》2024年5期)
□张建鲁
一
半湖青翠的芦苇和湖水一起荡漾,半湖红绿相间的荷莲随风飘香。盛夏时节的某个上午,我到微山湖观光采风,驱车乘船来到烟波浩渺、四面环水的微山岛一侧的神牛岛上,住进了“茅棚雅居”。“茅棚雅居”的一侧是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的藏书楼,一侧是湖人书屋。这个临湖而建的雅居本来是我的恩师——著名作家殷允岭先生的“行文别墅”,但他由于各种忙,平时也不怎么在这儿居住,就让他一个姓刘的远房亲戚在这里看家守院,帮忙照看果木花草,打扫卫生。恩师的这个刘姓亲戚看上去七十岁左右,个头很高,瘦削挺拔,大眼睛,深眼窝,皮肤有些黑,但精神头很好。有时他爽朗一笑,湖边柳树上的水鸟就吓得立马飞走,但总体看上去,他仍然还是文绉绉的。
当天中午,这个刘姓亲戚把我安置好,让我喝着荷叶茶,稍事休息,他便手脚爽利地忙碌起来,炖好了一锅鲫鱼和嘎鱼。我俩对饮小酌,三杯小酒下肚,他就笑着对我说:“你不要叫我刘老师,都不是外人,你直接叫我老刘就行,叫刘大哥也行。你一叫我刘老师,我心里就不得劲儿,就不是味儿……”
我一边站起来给他斟酒,一边有些疑惑地说:“那好吧,真的都不是外人,我就叫你刘大哥吧。不过,在我们本地一般都是称呼老师的。即便不是教学的教师,一般也都这么称呼。你咋说听着不得劲儿,不是味儿呢?”
他示意我再抿半口小酒,神思变得有些恍惚地说了半句:“这事说来话长啊……来,喝干它!”
他似乎想岔开话题。
我来这边,不就是来寻找创作素材、采风的吗?“说来话长”的事儿,我能轻易放弃吗?于是,我再次站起身,为他恭恭敬敬地斟酒,并用打火机为他点燃一根烟:“刘大哥,偌大的神牛岛,今儿就咱哥俩,而且我此行就是来湖区采风、找人聊天的。你刚才说的不得劲儿、不是味儿的事儿,我还真想听听,说不定就是个不错的素材,就可以以你为主人翁写一篇不错的作品出来,这也算是咱哥俩的缘分啦!”
他使劲抽了两口烟,愣愣地看着我:“这事吧,说起来还真有写头,我曾经想自己写写的,也给你老师讲过。但他说这事有头无尾的,是个不好把握的素材,写不好会出问题的,而且是‘历史’性的大问题……”
他还是有些放不开,似乎不想讲。
我又和刘大哥干了一杯,并反复夸奖他的厨艺好,居然把鱼烹饪出了浓浓的中药味儿,而且基本没有鱼腥味了。他小酒一喝,好话一听,渐渐有些激动,有些眉飞色舞了。我一看成色差不多了,就又鼓动他说:“刘大哥啊,有问题的事儿、不好把握的事儿,咱不会不写啊?光听听还能咋的!”
他终于开心、放心地笑了。一边喝酒,一边向我讲起他的往事、爱情和一肚子的委屈。
二
原来,他曾经是学校的高材生,而且当了一名公办教师。一场令他措手不及的师生恋,一场“拖泥带水”的师生恋,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师生恋,不仅让他失去了教师资格,还让他蒙受了多层的不白之冤。
他是湖区第一批高中生,学习成绩特别优异。就在乡、县两级教育部门准备保送他去北京读名校时,由于湖区师资严重欠缺,他为了让更多的湖区孩子有学上,果断留下来成为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后来又调到县里任高中语文教师。
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命运也就从这里拐弯了。
他当高中教师的第二年,文革开始了。他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却做了高二毕业班的班主任。有一天,校长突然找他谈话,说已查明,他班里有一名女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女儿。尽管这名女生的父亲在淮海战役的炮火中失踪了,再无法准确考证。作为遗腹子的这名女生也是反动派的狗崽子,也不能再让她做班干部了,更不能做共青团员了。
刘大哥知道,校长说的这名女生是他代课班级的班长和团支书史根红。因为红卫兵在抄她的家,她已经两天没有上课了。因为这事,刘大哥心里七上八下的。史根红可说是他最喜爱的学生之一,不仅出落得清秀靓丽,而且特别懂事,善良而聪颖。
校长找他谈话的当天夜里,他越想越不得劲儿,知道史根红的班长和团支书肯定保不住了。而且他也担心只有母女俩的史家被抄之后会是个什么处境,更是牵挂史根红目前的处境。这天晚上八点过后,他趁着夜色,悄悄徒步走到县城西郊史根红的家里。当他看到史根红的家已经被砸得乱七八糟,目睹她娘俩早已哭红的眼睛时,他的眼底一阵一阵的火辣。他对史根红说:“也许很快就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你要坚强……你,你永远是我们班的班长和团支书!”
“不,刘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再这样说了,你一定要和我划清界限!我也不可能再回学校了……我的书包都被没收了……”史根红边说边流泪。
刘大哥就安慰她说:“暂时不回学校也好。书包被没收了不要紧,我得空就过来给你补习功课,直到你学完高二的全部课程。”
“不,不!刘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再来我家了。万一被他们碰见或逮着,我们就都完了!你没必要因为我、因为我家而葬送了你自己的锦绣前程!”史根红说着说着居然不哭了,突然变得坚毅而坚定。
他忘了那天夜里是怎么回到学校宿舍的,大脑一片空白。他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三
尽管史根红非常坚定地拒绝了他补课的善意,甚至拒绝了他的关心和牵念,但他还是趁着夜深人静为她送去课本,并多次去她的家里嘘寒问暖,送去吃的喝的。
半年后的毕业季,下午上课之前,一位刚进校门的男生在去校园厕所的小径上神色紧张地塞给他一个封口的小信封,说是史根红托他转交的,并说史根红说,让老师下课后再看……
他赶紧塞进衣兜,急匆匆地躲进他的单身宿舍打开了那个小信封。他看着眼前的隽秀字迹,心里却突然惊慌失措。
他拆开了史根红的信。
尊敬而亲爱的刘老师: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学生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我原本是非常热爱这个世界、热爱生活的,可是,这个世界不仅不能容下我,还异常残酷地给我致命一击……
你的学生给你写这封信的心愿是,在我走后,在你说的一切过后(如果真的有那一天),你尽可能地照顾一下我苦命的娘亲……
你不要寻找我,更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我母亲)。我永远是你的学生,永远是微山湖的湖妹子。切记,切切记,你千万不要打捞我,让我静静地沉睡在湖底吧,求求你,亲爱的小老师(其实,你只比我大两岁,你是这个世界上,除了娘亲之外,唯一让我相信、唯一让我感念的人……)。
你的学生:根红
1968年6月29日
“叮铃铃”的上课铃声里,他飞也似的跑出宿舍,跑出校门,朝苇荷茂密的湖边拼命跑去。
离湖还有二三百米的树林野草间,他远远看到行动缓慢、一瘸一拐、晃晃悠悠的史根红的背影。他赶紧甩掉鞋子(他怕史根红听到他的脚步声加快脚步),飞一般地奔向她,扑向她。
湖水边的草地上,史根红被他扑倒的瞬间,她嘟囔着:“刘老师,你对不起我,你不守约!”
四
把史根红扑倒之后,刘大哥才看清,她的手里提着一条长裤,长裤的两条裤腿都被打了死结,里面装满了砖头和石块——她是决意要与砖石缠在一起永久沉水的。
他哭了。
她看到他的双脚都被芦苇扎破,汩汩地流血,她也哭了。
她赶紧将裤管里的砖石倒掉,用力将裤腿撕成布条,给他包扎止血。还在他肩头狠狠地捶了几下。
但是,无论他再怎么劝说和开导,她就是不答应回家。她还说,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她的心已经死了,她已经死定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这一切。刘大哥陪着她直到深夜,直到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公安拿着手电筒赶来。
因为下午第一节课就是他的,而且很多教师和学生都看见他飞快地跑出了校门,还有学生看见他跑向了湖边。校长看他到天黑也没回学校,就报了警。
二人被公安送进了县医院并连夜审问。看着史根红已经凸起的肚子,公安首先怀疑是刘大哥诱奸或者强奸了她,才导致了湖边寻死的一幕。直到这时,刘大哥才注意到史根红凸起的肚子。
为了还刘大哥清白,关键时刻,史根红说出了强奸她的人是造反派的头头。
但是,医检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腹便便的史根红还是处女。由于怨恨、气恼或者饮食问题,她肚子里生病了,长了个大瘤子。刘大哥花尽了所有积蓄,并跪求医生,给她做了切除手术。
问题是,她为啥怀疑自己是被强奸怀孕的呢?
后来,直到刘大哥和她结婚之后,谜底才被揭开。有一天傍晚,她去为感冒的娘买退烧的药片,正巧被路过的造反派头头看到了,并以问话为由,强行拉她到了无人的一角。她的衣服也被撕扯了,人也趴她身上了,但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造反派的头头就骂骂咧咧地提裤子走人了。按刘大哥的话说,应该是生理原因,造反派头头没能成事。
这也许就是常说的万幸,或者天意。
五
但不幸的是,刘大哥却因此受到了牵连。有人说他俩早就眉来眼去;有人说在校园搞师生恋罪该万死;有人说捉奸捉双,他俩被人在湖边的草滩逮个正着……流言蜚语,满城风雨。
刘大哥很快被学校开除,并背上了百口莫辩的骂名。
也许是为了刘大哥,本来决意赴死的史根红,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不再寻死觅活,还回过头来安慰起了刘大哥。她说:“哪怕整个世界都背弃你,你起码还有我!”
接下来,无职一身轻的刘大哥带着大病初愈的史根红和她的娘亲回到了乡下的自己的家。他和史根红结婚,生子,过上了平常百姓虽困苦但却长久的幸福生活。
说起史根红大嫂的身世,刘大哥说,他老岳母曾经说过,根红的父亲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秘人物,即便是家人,也一直没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在根红母亲的一再追问下,他曾对根红的母亲说:“我上对得起家国,下对得起亲人,你不会嫁错人的!”还说“根红”这个名字就是在根红的母亲刚怀孕时他亲自给起的,并说天快亮了,无论生男生女,乳名都叫红儿,长大后就叫根红,那时候这名字就给定下了。
听到这儿,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就问刘大哥:“你岳父的名字你知道吗?后来到有关部门查询过吗?”
刘大哥说:“知道啊,叫史可鉴,但在国民党淮海战役的阵亡名单里查不到这个名字,在解放军淮海战役的阵亡名单里也查不到这个名字。这最后成了一个死案,成了一个谜了。”
听到这里,我的心头猛地一震——我听父亲说过,他的战友中有一个叫史什么的,最后不知下落了,再也找不着,查不到了。父亲还说,他所在的解放军微湖支队,尽管没有情报部门,在解放战争中却曾有三位战友作为“探子”,要么渗入敌占区、要么打入敌人内部,为战争的胜利,尤其是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过看不见、甚至是无以考证的巨大贡献。难道刘大哥的老岳父就是我父亲说过的那个失踪的战友?难道真就有这么无巧不成书?
六
带着巨大的疑问,我邀上刘大哥一起回到兖州,来到我九十多岁的老父亲身边。
当刘大哥提到“史可鉴”这三个字时,我年迈的老父亲突然从沙发上站起:“你是谁?你咋知道这个名字的!”
刘大哥就把来龙去脉又在我老父亲面前重复了一遍。我老父亲听着听着就流泪了,最后真的是老泪纵横,他喃喃自语道:“胡西明啊,我的老战友啊!解放后我到微山县、鱼台县、徐州等地查找过你多次,就是找不到你的下落,也找不到你家人的下落,今天你的女婿却找上门来了,天啊……”
听说刘大哥的老岳母还健在,我的老父亲当即对我说:“走!我跟你俩马上回微山,去看望我老战友的遗孀,去为我的老战友正名,去为我的老战友平反昭雪,去为我的老战友立碑立传!”
于是,老父亲带上他刚领到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急急火火地上车,急急火火地赶往微山。
在路上,老父亲说:“胡西明同志不仅是解放战争的烈士和功臣,也是抗日战争的功臣。我们曾经一起和日本鬼子多次鏖战,他智勇双全、英勇善战,抗战时就是功绩卓著的侦察兵……我的这枚纪念章今天就转送给他!”
见到刘大哥的老岳母之后,一说一叙,老人家立马泣不成声。她说她也不知道丈夫在部队还使用过“胡西明”这个化名,难怪怎么也查不到他的下落。
我的老父亲就说:“这是军队的纪律,而且是铁的纪律,可鉴被派往敌占区时使用的化名,除了我自己知道,任何人都不得知晓,这是单线联系啊。可是,解放后我曾多次四处寻找你们的下落,每次都是失望而归。当时,你和孩子去了哪儿啊?”
刘大哥的老岳母说:“他失踪之后,有个老乡是地方武装的头头,他说可鉴被俘虏了,可鉴投敌了,还当上了营长,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的炮火炸死了。我一听,这还了得?我就带着根红躲到乡下的亲戚家去了,好多年之后,感觉没事了,才又回到了夏镇西郊的家中。”
老父亲就说:“你家里还有可鉴的衣帽之类的吗?我要为他立碑!”
刘大哥的老岳母说:“衣帽没有了,只有一双他穿过的布鞋,还是我亲手纳鞋底做的。我对红儿曾经说过,只要你父亲的这双布鞋在,你父亲就没走远,就永远和我们一起……”
根红大嫂这时再也忍不住,抱着那双里三层外三层用蓝布裹着的布鞋号啕大哭。
半个月之后,石碑刻好了。老父亲又和我一起来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微山湖畔,亲自为他的战友史可鉴同志的布鞋墓铲土奠基。
老父亲决意把那枚纪念章也与那双布鞋葬到一起,被根红娘俩拒绝了。根红大嫂说:“在您老的过问和证实下,现已查明和落实了我父亲的身份,这就是对我父亲最好的抚慰和纪念!”
半湖青翠的芦苇和湖水一起荡漾,半湖红绿相间的荷莲随风飘香。英烈的鞋墓石碑临湖而立,倒影依依……
选自《北方文学》2024年5期

